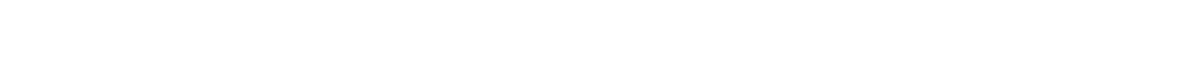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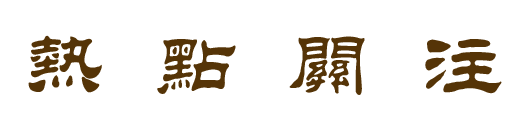

(注:此文系北京三式乾坤信息技術(shù)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景磐先生之作)
壹、前言
長期以來,學(xué)界一直抱持著兩種共識:一個是《易經(jīng)》為占筮之書,而占筮屬于迷信;另一個是《易傳》為義理之書,義理屬于哲學(xué)。
康學(xué)偉先生在論述金景芳先生所屬易學(xué)流派時,亦曾指出:
古來治《易》者大抵分為兩途:一是精英易學(xué),二是繼續(xù)沿卜筮道路發(fā)展的江湖易學(xué)。后者在漢代已被納入數(shù)術(shù)中,與經(jīng)典易學(xué)分道揚鑣了。
康先生又說:“義理易學(xué)當(dāng)推儒學(xué)《易傳》,孔子用哲學(xué)的語言解釋了難懂的卜筮語言,顯微闡幽,揭開了《易》的思想內(nèi)涵和哲學(xué)本質(zhì)。”又說:“金先生一貫高揭義理派大旗,明確說他對《周易》的解說恪遵孔子《易大傳》所開辟的道路,研究的著眼點不在卜筮而在于《周易》所蘊藏的豐富思想內(nèi)容。馬王堆帛書之《要篇》記載:子貢問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則明確回答:“吾觀其德義耳。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先生晚年得見孔子此語,深感千古上下同此一心,因先生一生治《易》所孜孜以求者,正在于“觀其德義”。(見《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
康學(xué)偉先生以上論述,代表了當(dāng)前易學(xué)界的主流觀點,但某些方面不無偏頗之處。被譽為當(dāng)代最為著名的《易》學(xué)家之一的金景芳先生,也只在“觀其德義”這一點上,與孔子“千古上下同此一心”,而在孔子“吾百占而七十當(dāng)”對占筮的包容性上,則大相徑庭了。
筆者于此想要說明的問題是,歷史上經(jīng)典《易》學(xué)的經(jīng)營者固然都是精英人物,而江湖《易》學(xué)的經(jīng)營者們,也并非皆是“下九流”的江湖術(shù)士。
清代官方編纂的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和當(dāng)代編纂的《續(xù)修四庫全書》中,收錄古代占筮術(shù)數(shù)學(xué)作品有百部之多,其中不乏流傳千古的不朽之作,如《焦氏易林》、《京房易傳》、《太玄經(jīng)》、《皇極經(jīng)世》、《三易洞璣》等,其經(jīng)營者中也不乏叱咤風(fēng)云的曠世奇才。
三百年前,西方學(xué)者白晉首先從兩張先天六十四卦圖中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已成為電子計算機語言的二進位制數(shù)學(xué),而這兩張《易》學(xué)圖就出自被視為術(shù)數(shù)學(xué)作品《皇極經(jīng)世》的作者邵雍之手。現(xiàn)代有學(xué)者指出,西漢楊雄的《太玄經(jīng)》中是三進位制,而三進位制將會成為創(chuàng)造光子計算機的語言。當(dāng)然,這個三進位制還有待進一步論證和發(fā)掘。但不可否認,中國古代的占筮術(shù)數(shù)學(xué)與現(xiàn)代自然科學(xué)在某些方面是有聯(lián)系的。
我國的正史中,如《史記》的《龜策列傳》、《日者列傳》,其他正史的《五行志》、《方伎列傳》等,記載了歷代術(shù)士及數(shù)術(shù)學(xué)家的神秘事跡。《漢書藝文志》將數(shù)術(shù)分為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四庫》總目分為數(shù)學(xué)、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等。史書所列數(shù)術(shù)圖書,其子目有風(fēng)角、九宮、太乙、奇門、六壬、易占、堪輿、陣圖之類。還有歷代流傳下來的數(shù)以千計的占筮術(shù)數(shù)案例。雖然這些資料不無糟粕荒誕的成分包含在內(nèi),但也應(yīng)看作是文化遺產(chǎn)的一個組成部分,絕不應(yīng)該一律排斥在研究大門之外。
筆者認為,首先應(yīng)當(dāng)解決好對《周易》占筮和術(shù)數(shù)學(xué)的幾個認識問題,消除偏見,才能推動探討研究走上正確的軌道。
貳、卜筮的意義與價值
一、《周易》是一部筮書
《周易》是一部筮書,《易傳》講義理又講占筮,既介紹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一般認為,《易傳》(又稱“十翼”)為孔子所作,是義理學(xué)著作,孔子的功績就在于在《易傳》中完成了《易經(jīng)》由占筮向哲學(xué)的轉(zhuǎn)變,由此開了易學(xué)哲學(xué)的先河,甚至稱孔子是摒棄占筮的,孔子對《易》只“觀其德義”[1]。這種觀點無疑是片面的,今天《易傳》中有關(guān)幾段原文,加以分析:
大衍之?dāng)?shù)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后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dāng)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dāng)萬物之?dāng)?shù)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2]。(《系辭上》第九章)
這是對《周易》占筮方法的最早也是最直接的介紹。字里行間充滿對筮法的崇尚和贊揚,最后一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及畢矣”更是充分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常其變,以制器其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3]?(《系辭上》第十章)
占筮雖為“四道”之一,在孔子心目中卻占據(jù)著極為重要的位置。因為緊接著他指出,君子將有所作為,有所行動之時,用《周易》揲蓍占問而據(jù)以發(fā)言行事,《周易》就能如響應(yīng)聲地回答問題,不論遠近或是幽隱、深邃的事情,都能推知將來的物狀事態(tài)。這里著重贊揚了占筮的神奇作用。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代用[4]。(《系辭上》第十一章)
探賾索引,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兇,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5]。(《系辭上》第十一章)
把蓍和龜看作神物,而這種有靈性的蓍龜是上天神的意志的體現(xiàn),圣人據(jù)此設(shè)立用蓍草、龜甲進行占卜的方法,教給人們進行占卜,以達到趨吉避兇的目的。在孔子的心目中,占卜能夠探尋求索深奧隱晦的道理,鉤取招致深處遠方之物,能夠成就天下之人的勤奮作為,因此說蓍占龜卜能夠決天下人之疑,使人勤勉向前,成就事業(yè),其作用最大。
孔子在《易傳》中對占蓍給出了定義,那就是“極數(shù)知來之謂占”(《系辭上》第五章),他認為數(shù)是能夠“成變化而行鬼神”(《系辭上》第九章)的,當(dāng)然占耆的效用是“占事知來”(《系辭上》第十二章),由 知未來的導(dǎo)向中以決定趨避,把事業(yè)做好。并且孔子提倡“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系辭上》第二章)是倡導(dǎo)有所行動就要請教占筮的,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系辭上》第二章)
在《孔子家語》等書中還記有孔子自己所作或令弟子所作的筮案有五例。而孔子在《論語》中又說“不占而已矣”。在近年出土的帛書《要篇》中,孔子還說:“《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觀其德義耳也。”這似乎在孔子本人身上,對占筮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態(tài)度。怎樣看待這種矛盾現(xiàn)象呢?在《論語》和《要篇》中,孔子是摒棄否定占筮嗎?
孔子是晚年才研究易學(xué)的。孔子自己說他五十歲“知天命”,六十歲“耳順”,七十歲“隨心所欲不逾矩”。晚年的孔子,學(xué)識很淵博,人生、社會經(jīng)驗很豐富。這樣一個成熟老到的人,當(dāng)然是“不占而已矣”,他怎能看重近似江湖術(shù)士的祝巫們呢?《要篇》中已有很好的注腳。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shù),明數(shù)而達乎德,有仁【存】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shù),則其為之巫;數(shù)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6]。”
對上述這段話應(yīng)從兩個方面理解其實質(zhì):一是孔子鄙視學(xué)識短淺的史巫之筮,并不等于鄙視周易占筮;二是孔子重行德義而不為自己妄求福吉,這與“敬鬼神而遠之”也是一脈相承的。清人江永有一段對卜筮的論述,也有利于幫助人們加深理解。江永說:
卜筮之道,先人謀而后鬼謀,事有當(dāng)行當(dāng)止,斷以義,無事謀諸鬼神也。《志》曰:“圣人不煩卜筮。”又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惟事有猶豫,或關(guān)系重大,乃以筮決之。若瑣屑小事,無用筮也,未來之休咎亦聽之。問諸鬼神,多憂多疑,方寸徒增膠擾。《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畢竟觀象玩辭之時多,觀變玩占之時少。(見《河洛精蘊》)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并非摒棄否定周易占筮的價值和作用,這在《要篇》中也有明確記載:
子貢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dāng)。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
趙均強先生將這句話譯為:“孔子說:過去我自己占卜,大概一百次有七十次是沒有疑問的吧。即使像周梁山崩后那樣著名的共筮占例,也還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罷了。”一百次占卜能夠應(yīng)驗七十次,其應(yīng)驗率還是值得肯定的。在《易傳》和《要篇》中,孔子對占筮的態(tài)度是鮮明的,也是肯定的,同時也是一貫的。可以肯定地說,孔子在《易傳》中既詳述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講義理而不廢占筮,是義理與占筮二者并重的。
二、 古人將卜筮列為重大決策的必然步驟和環(huán)節(jié)
占筮術(shù)數(shù)曾經(jīng)成就了歷史上許多風(fēng)云人物的業(yè)績,鄙視占筮術(shù)數(shù)是后世儒家之陋。在《尚書?洪范稽疑》便已如此記載: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這是指國王等大人物有大的決策行為,首先要自己深思熟慮,還要征求卿士的意見,也要聽取老百姓的意見,最后要進行卜和筮(卜是灼龜,筮用蓍草演算求出卦爻。今人認為卜法已經(jīng)失傳,筮法由《周易·系辭》中的記載而流傳下來)可見在古代卜和筮是重大事件決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司馬遷稱“五謀而居其二”,卜筮在決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尚書·洪范》又說: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nèi)吉,作外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兇[7]。
從上述幾種決策情況可以看出,龜筮占卜的意見,在決策中所占比重已經(jīng)超過國君、卿士和庶民三個方面的意見。龜筮占卜在決策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宋人蔡沈在注解《尚書》這段話時指出: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指人與龜筮占卜的意見相一致——引者)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nèi),不可作外,內(nèi)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指占卜的意見與國君、卿士、庶人的意見違背——引者),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
在古代龜筮占卜活動不僅登上大雅之堂,參與廟堂軍國大事的決策,并且“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對于卜筮人的選擇是很嚴格的,同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對于占卜意見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也可見是慎之又慎的,唯恐有誤。
西漢史學(xué)家司馬遷也充分肯定了龜筮占卜的地位和作用。他說: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此指西漢前期平定諸呂之亂后,代王劉恒入朝即帝位——引者),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8]。(《史記·日者列傳》)
自古圣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yè),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jù)禎祥。涂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9]。(《史記·龜策列傳》)
聞古五帝三王發(fā)動舉事,必先決蓍龜[10]。(《史記·龜策列傳》)
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zhàn)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11]。(《史記·龜策列傳》)
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12]。(《史記·龜策列傳》)
古代是以人謀和卜筮并重的。人的思慮往往只能顧及事物前進發(fā)展的必然性的因素,而不可能預(yù)知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卜筮則能填補人的思慮所達不到的領(lǐng)域,正好補充人謀的不足,二者是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周易》稱卜筮為“鬼謀”,“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系辭下》第十二章)也是提倡人謀與占筮二者相結(jié)合的。先天易學(xué)的創(chuàng)立者邵雍曾說: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皆曰可,則事成而吉也。(《皇極經(jīng)世·觀物外篇》)
人謀是人的意志,鬼謀是天的意志,只有二者相一致時,才是吉祥的,這與《尚書》所稱人與龜筮皆從是謂之大同是相一致的。
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古人用于重大決策的案例很多,散見于正史、方志及名家著作。唐明邦先生歸納并舉例說:
一是重大政治舉措的決策,要進行占筮。如重耳返國,晉悼公為君,勾踐歸國,南朝宋順帝禪位,宋徽宗被俘,溥儀論國民政府等;二是重大戰(zhàn)爭,須通過占筮預(yù)測是否可行及未來勝敗結(jié)局,如鄢陵之戰(zhàn),趙鞅救鄭,韓原之戰(zhàn),吳王伐齊,漢武帝伐匈奴,鄧艾伐蜀,張康論伐日本,奉直戰(zhàn)爭等;三是個人重大行動的抉擇,如伍子胥奔吳,夫差釋勾踐,李綱仕唐,朱熹焚奏稿,辛棄疾南歸,紀曉嵐科舉等。(《中國歷代易案考·序》)
在古代不僅漢民族有遇事進行卜筮的習(xí)慣,各少數(shù)民族亦有決疑之卜,只是占卜的方法和所用道具各不相同,這就是“國不同俗”。在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中,各種方式的卜和筮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傳統(tǒng)民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不可否認,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風(fēng)云人物都是精通占筮術(shù)數(shù)的,也可以這樣說,占筮術(shù)數(shù)曾經(jīng)成就了不少歷史風(fēng)云人物的業(yè)績。如《諸葛丞相集》記載:
(諸葛亮上先主書有云)亮算太乙數(shù),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酉方,又觀《乾象》,太白臨于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兇少吉。
按《太乙飛鈐》云:先主自涪攻雒城,亮遣馬良上先主書。巳而,軍師龐統(tǒng)中流矢死。
諸葛亮為成就蜀漢帝業(yè)立下了汗馬功勞,這除了他的雄才大略之外,與他推演太乙數(shù)、觀天象等也不無關(guān)系。再如唐高宗時的檢校右衛(wèi)大將軍裴行儉《新唐書·裴行儉傳》中說,裴精陰陽術(shù)數(shù),每次出征,都能提前測出勝利日期。傳中有兩則具體事例較為突出:一是儀鳳二年,詔命裴行儉護送波斯王回國并兼任安撫大食使,途徑莫賀延磧無人區(qū),“風(fēng)礫晝冥導(dǎo)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少安,俄而云徹風(fēng)恬,行數(shù)百步水草豐美,后來者莫識其處。”二是調(diào)露元年討伐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徏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徏之,此夜風(fēng)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余,眾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令第如我節(jié)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清人王宏撰《周易筮述》卷八記載此案曰:行儉“袖傳一卦,遇習(xí)坎初爻,曰:主有大水,不利,邃令移就崇崗”。
《明史·劉基傳》記載:
基博通經(jīng)史,于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xué)。當(dāng)朱元璋聘請劉基至應(yīng)天府(今南京)軍中,即向朱“陳時務(wù)十八策”,“陳天命所在”。至于其所陳時務(wù)十八策,現(xiàn)已不得其詳,而“陳天命所在”一語,則明顯屬象緯之學(xué)用語。當(dāng)踞于上游的陳友諒稱帝后,以數(shù)倍于朱元璋的兵力向應(yīng)天進犯之時,諸將 議或投降或逃跑,惟劉基向朱元璋密陳“天道后起者勝”的計策,大敗陳友諒。“天道后起者勝”為太乙式用語。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率師二十萬迎戰(zhàn)陳友諒六十萬大軍于鄱陽湖。
《劉基傳》記載曰:
與友諒大戰(zhàn)鄱陽湖,一日數(shù)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戰(zhàn),基侍側(cè),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zhèn)}促徏別舸,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
湖中相持三日未決,基請移軍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決勝[13]。
如果說劉基令朱元璋更換所乘舟船,是激戰(zhàn)中急中生智所為,那么,劉基料定決勝日為金木相克日,則為術(shù)數(shù)學(xué)中五行生克用語。而該戰(zhàn)役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二十丁亥日兩軍相遇于康郎山,經(jīng)過激戰(zhàn)決勝日為七月二十四辛卯日,正是金木相克之日。劉基于洪武四年歸老回鄉(xiāng)后:“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
當(dāng)劉基臨終時“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后人習(xí)也’”當(dāng)然,劉基深知研習(xí)天文術(shù)數(shù),弄不好會招來殺身之禍。《明史·劉基傳》中還說,劉基與太祖朱元璋“帷幄語密,莫能祥,而世所傳為神奇,多陰陽風(fēng)角之說,非其至也”。又說:“基以儒者有用之學(xué),輔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纖緯術(shù)數(shù)妄為傅會,其語近誕,非深知基者,故不錄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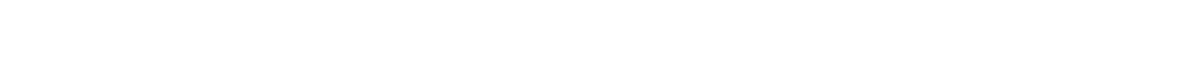
楊懿人老師個人官網(wǎng)
Yang Yiren's official website
聯(lián)系電話:13621280499
郵箱:zhouyi64@163.com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qū)草園胡同76號聚才大廈A座206室
關(guān)注我們
 掃碼關(guān)注公眾號
掃碼關(guān)注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