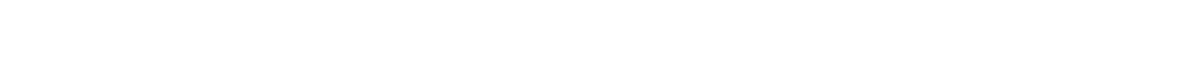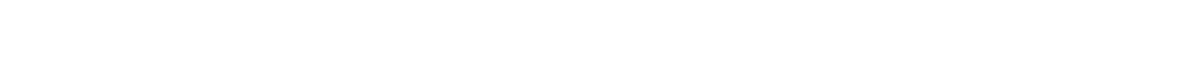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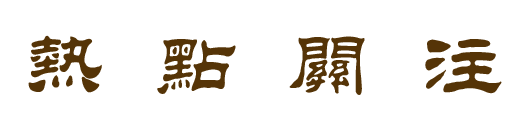
(文/楊景磐)
西漢哲學家揚雄仿周易作《太玄》(后人稱為《太玄經》),其中筮法是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太玄》原文和原注對筮法的論述簡略,或因年代久遠,在流傳過程中傳述或者傳抄有誤,致使后人對太玄筮法產生歧義。唐宋以來,對于太玄筮法有多種版本流行,不能統一。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個世紀后期,中華書局出版了劉韶軍先生點校的《太玄集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鄭萬耕先生的《太玄校釋》,這說明《太玄經》已經引起當代學者的重視和研究。但是,點校的《太玄集注》,對其中筮法部分未能做出任何有價值的點校。《太玄校釋》對其中筮法雖作了較詳細地校釋,但未能對前人的不同觀點作詳細考證,不能明辨正確與錯誤。鄭萬耕先生僅憑己意作了不同前人的新的闡釋,可惜,這些闡釋非常片面,難以從《太玄經》原文、原注中找到依托。
為了認真嚴肅地開展學術研究和探討,正本清源,還太玄筮法以本來面目,筆者冒昧寫下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太玄筮法原文、原注(摘錄自四庫全書本《太玄經》):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原注:謂一二三也。一二三各三變凡三十六也,視此之數而為策。)天以三分,終于六成,故十有八策。(原注:天以三分,謂一二三也,因而六之,故言終于六成,成十八也。)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原注:天位有九,地位有九,陰不下陽,陽不施陰,故曰不成。因此十八位其大數為三十六,故言因而倍之也。虛,空也。扮猶并也。空地三以下于天,天施地成,滋生二萬三千之策。三十者,三十三也。)別一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余,以三搜之,并余于艻。(原注:艻猶成也。今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為艻,蓋以識之也。中分其余,亦左手之二指間,以三搜之以象三光,其所余者,并之于左手兩指間,故謂之艻,蓋以識揲者之數也。凡一掛再艻以成一方之位,通率四位,四掛以象四時,八揲以象八風,歸余于艻以象閏也。)
一艻之后而數其余,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原注:處下方州部家之數也,七八九以成四位,然后首名定也。)六算而策道窮也。(原注:謂余得七則下一算,得八則二算,得九則下三算,一二三凡六揲三十三止,得六算,故言窮也。窮則揲以成四位,不出七八九也。)
以上為有關太玄筮法的原文和原注,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最為原始的資料,也是最重要最關鍵的資料。我們推演太玄筮法,只有符合上述這些原始資料的要求,才能算是正確的,否則,就是不正確的。
其實,上述原文和原注中,對于太玄筮法的基本要素都講出來了,太玄筮法要備三十六根蓍草,具體推演時要抽出三根放在一邊,以表示“地虛其三”,只用三十三根。在三十三根蓍草中,要先取出一根掛在左手的小指間,稱之為“別一”。然后“中分其余。以三搜之,并余于艻”。通過“一掛再艻以成一方之位”。要由方州部家四位才能確定一首之名。方州部家四位要通過“四掛、八揲”和“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的計算來完成。
由于原文和原注文字簡略,或者因年代久遠,傳抄有誤,致使原文、原注語意不能連貫,使后人產生歧義。唐宋以來,對于太玄筮法也有多種版本流行,不能統一。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是正本清源,使太玄筮法回復其本來面目。
二、唐王涯論太玄筮法(摘錄自《太玄集注》附錄《王涯說玄》):
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以扮天,(扮,配也。)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玄筮以三十三策。令蓍即畢,然后別分一策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余,以三揲之,并余于艻,(此余數欲盡時,余三及二一也。)又三數之,(并艻之后,便都數之,不中分矣,前余及艻不在數限。)數欲盡時,至十已下,得七為一畫,余八為二畫,余九為三畫。凡四度畫之,而一首之位成矣。
按王涯此論,是三十六根蓍草除去三根不用,只用三十三根。先掛一根于左手小指間,余下三十二根分為左右兩部分,以三根為一組數這兩部分蓍草,或余一,或余二,或余三。余數與掛在左手小指間的一根合并(并馀于艻)。再把所余兩部分蓍草合并一起,不再中分,再以三根為一組數至十以下,余七為一畫,余八為二畫,余九為三畫。如此共做四次,就可組成一首。
王涯此論,語意雖連貫,但卻最后得不出七、八、九來,不能應用,三十三根蓍草掛一(即別一)之后,余下三十二根,分為左右兩部分:
左 右
1 | 1 |
2 | 3 |
3 | 2 |
以三根為一組,分數左右兩部分,左余一則右必余一,左余二則右必余三,左余三則右余二,左右兩部分之余數或二或五,所余正策則為(32-2)三十或(32-5)二十七。若用三數數至十以下,三十得余數九,二十七亦得余數九,得不到八和七。因此,王涯此論太玄筮法是錯誤的。
三、宋司馬光論太玄筮法(摘自司馬光《說玄》):
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
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余,以三揲之,并余于艻,一艻之后數其余,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
司馬光此論與王涯無異。“一艻之后數其余”,得不出或七、或八、或九三個數。除非對“一艻”另作解釋。司馬光文中既對“一艻”未作說明,故仍屬紙上談兵,不得實用。
四、宋許翰論太玄筮法(摘引自《太玄集注》卷八):
天以三分,則一二三,綜而為六。以六因三,為十有八。天施而地成之,是以倍為三十有六。此神靈曜曾越卓之數也。地則虛三以受天,故策用三十有三。玄筮掛一者,至精也。中分而三搜之者,至變也。余一二三則并于艻者,歸奇也。一艻而復數其余,卒觀或七或八或九,則畫一二三焉。天以六成,故六算而策道窮,則數極而象定也。得方求州,得州求部,得部求家,是謂散幽于三重而立家。凡四筮。
許翰之論與王涯、司馬光皆相同,仍然于“一艻”之后得不出七、八、九,則不可能畫一、二、三,更不可能得方求州,得州求部,得部求家。
五、明葉子奇論太玄筮法(摘自《太玄本旨》):
揚子謂極一為二,極二為三,極三為推,故玄以三為天之本數,二其三則六,故以六成。六其三則為十八,所以為天之策也。天茍不施,地則何成?因以天之十八策而加倍,則為三十六策。然天常有余,地常不足,故虛地之三以扮并天之十八策,占用三十三策也。
揲時別以一策掛于左手小指間,以準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義,然后以其余三十二策而以三揲之,并其欲盡三及二一之余數,而艻于左手二指間。
一艻之后,將三搜之策又都以三數之,不復中分,數欲盡時至十以下,得七為一畫,余八為二畫,得九為三畫,其前掛及余艻不在數限。
凡四度畫之,而方州部家之位成,而首之名定矣。
故自立天地之策為三十六是一算,虛三是二算,掛一是三算,分搜是四算,并艻是五算,數余是六算。此一揲之策道窮也。
葉氏之文是明晰如口述,通俗易懂,但仍是墻上畫餅,不得實用。因為葉氏所述與王涯、司馬光、許翰所論并無區別,最后仍然得不出七、八、九,雖“四度畫之”,亦然得不出方州部家之位。
六、今人鄭萬耕先生對太玄筮法的解釋
鄭萬耕《太玄校釋·太玄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
注[一四]:
筮時,從三十三策蓍草中取出一策,掛于左手小指間,是為“別一”。然后將其余蓍草隨意分為兩部分。“中分”之后,將其中一部分,按每三策一組數之,是為“以三搜之”。搜過之策,仍置于原處。在“三搜”之后,將剩余之蓍草(或一策,或二策,或三策)置于所掛蓍草之旁,是為“并余于艻”。
注[一五]曰:
筮時,“一艻之后”,再數另一部分,以三搜之,搜過之后,仍置原處。數至十以下,剩余者必為七、八、九策。其余七策為一畫,八策為二畫,九策為三畫,是為“定畫”。
注[一六]曰:
六算,謂“別一”、“中分”、“三搜”、“并余”、“再數”、“定畫”等六次策算。經此六算,即可定玄首之一位。
鄭萬耕先生的三則校注,概括了太玄筮法確定玄首一位的全部過程,實屬對太玄筮法較全面的敘述,可以說算是完備了。但是,很遺憾,鄭萬耕先生并未在揚雄《太玄經》原文、原注等原始資料上下功夫,而是摘取前人的一些片面的有關論述加以拼湊綜合,再加入己意,勉強得出“其余七策為一畫,八策為二畫,九策為三畫,是為定畫”的結論。這樣的結論,當然有臆斷之嫌,不能符合太玄原文、原注之本意。
綜觀鄭萬耕先生的三則注文,是將“別一”之后的三十二根蓍草隨意分為兩部分,取其中的一部分按每三策為一組數之,把數過之策仍放在原處,把余下或一策或二策或三策蓍草放在所掛蓍草之旁(應是掛于左手小指與無名指之間),此為“并馀于艻”。對于這一部分數過的蓍草已是棄之不用了(以下已看不到這一部分蓍草以及“并余于艻”的蓍草有什么用途)。
“一艻之后”,再取另一部分蓍草,仍以每三策為一組去數,數過的蓍草仍放回原處,數至十以下,余七策為一畫,余八策為二畫,余九策為三畫,此為“定畫”,為玄首一位。
鄭先生所述將三十二根蓍草隨手分為兩部分之后,取其中一部分三搜(以三根為一組去數)之后,并余于艻。然后,再取另一部分進行三搜,數至十以下或七或八或九為“定畫”。“定畫”是最后的結論。這個結論與第一部分的“三搜”和“并余于艻”不存在直接關系,也就是第一部分蓍草是否“三搜”、“并余于艻”,都不影響最后的結論。換另一句話說,就是被隨手分為兩部分的蓍草,可以直接取其中一部分“定畫”。這樣以來,第一部分的“三搜”和“并余于艻”都是無用之工。鄭先生所述的“別一”、“中分”、“三搜”、“并余”、“再數”、“定畫”等六算,可節省為四算。恐怕這樣減少程序就不符合太玄本意了。
另外,對第二部分蓍草“數至十以下”而定畫,在太玄原文和原注中都找不到依據。數“至十以下得七為一畫,余八為二畫,余九為三畫”,最早為唐人王涯所述,明人葉子奇復述此語。今人鄭萬耕先生對此重蹈覆轍,但這并不符合太玄原文、原注之意。
古人創立筮法,每一環節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義,后人不得任意減少和改變。
那么,到底怎樣做才能符合太玄原文、原注之意呢?請看下文。
七、南宋張行成論太玄筮法(摘自張行成《元包數義》):
太玄之蓍三十三于老陽用策之中,地虛三以拼天,天用三六,地用三五,為天地相交而互用者也。
玄為地承天之數,故用三而又虛三、掛一于三用之內也。
玄以三揲者,從天之三元也。兩揲成一重者,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地之兩也。四重為一首者,體之四也,玄別用九贊者,體用分兩也。
玄兩揲之奇,皆不三則六者,地除其二也。
玄通二揲而奇九,得天九而已。
玄之四重者,地之四體也。其初揲之暗數者,地中之虛用,故當物數也。玄一首之奇得九之四,并之而三十六,得易一爻老陽之策數。
玄之蓍本用老陽之策四之九,虛其三則為三之十一。用二十七者,為去二用九,用二十四者,為去三用八,用二十一者,為去四用七,是去其二三四之九而用其七八九之二十四也。九者,乾也,去之以存九天之用;二十四者,坤也,用之以立四重之體也。
易揲以四,玄揲以三,揲去其一蓍,易用六七八九之策,玄用七八九之策,去共六之一數。六者,坤之數,是為不用之一,其實則方州部家所以載其體,其虛則玄之所生也。
張行成此文主要是論述太玄筮法所用數以及推測過程中各環節的象征意義。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張行成對太玄筮法的認識以及張行成所主張的太玄筮法的程序和過程。
“兩揲成一重”,即兩揲成一位,“四重為一首”即方州部家四位組成一首(卦),“玄兩揲之奇,皆不三則六”,是初揲加掛一,余數不三則六。再揲不掛,余數也是不三則六。張行成指出,太玄通過初揲和再揲,會出現二十七、二十四和二十一三個用數,由這三個用數與九、八、七的關系來確定或三或二或一的一畫。
張行成在論說太玄筮法中提出的上述概念,與太玄原注中“一卦再艻”、“四位四掛八揲”和“七八九以成四位”等概念相吻合。可以這樣認定,張行成對太玄筮法的論述,比較符合太玄原文、原注之義。
八、清人黃宗羲論太玄筮法(摘自《易學象數論》):
(太玄)蓍之數三十有六。陽饒陰乏,地則虛三,故揲用三十三。三十三策之中,取一以掛,掛而后分也。
分為二刻,三搜左刻,置其余,或一,或二,或三;次三搜右刻,置其余如前數。其余數不二即五,掛策在外。
左 右
2 | 3 |
3 | 2 |
1 | 1 |
左二則右必三,左三則右必二,左一則右亦一。
以上初揲。在易為再扐,在玄為一艻之半。次除前余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三十,或二十七。不掛,不搜,如前法。其余數不三即六。
左 右
1 | 2 |
2 | 1 |
3 | 3 |
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亦三。以上為再揲。再揲之余,并之于艻,是為一艻。艻即所掛之一也。王制“祭用數之仂”。“鄭注”什一,掛先別于正數,故名艻。蓋再揲未竟,余數未并;再揲竟,則余數并入掛內。此所謂余,乃不用之數,與上下分數之余異。
再揲止一掛,故曰一艻。余數既并置之不用,而數其所得之正策:七其三為一,畫一;八其三為二,畫一一;九其三為三,畫一一一。以成一方之位。
如是每再揲而成位。自家而方,四位通計八揲,然后首名定也。
黃宗羲、張行成二家對太玄筮法的論述相同。其操作程序可整理為下:
三十六根蓍草虛三不用,只用三十三根。初揲是從三十三中抽出一根掛在左手小指間,將三十二根蓍草隨手分為左右兩部分。以三根為一組先數左邊的一部分,然后再數右邊另一部分。左余一則右也余一,左余二則右余三,左余三則右余二。
左 右
1 | 1 |
2 | 3 |
3 | 2 |
左右兩部分的余數不二則五,若加上掛于 左手小指間的一根,則余數或三或六。黃宗羲說初揲余數不二則五,是未加“掛一” ,張行成說不三則六,是指加上“掛一”。初揲后的余策應仿大衍之例,掛于左手無名指與中指之間,是謂歸奇于艻。
然后將初揲之后的正策合在一處或三十(33-3)根或二十七(33-6) ,進行再揲。仍然將蓍草(或三十根或二十七根)隨手分別左右兩分,先以三根為一組數左邊一部分,然后再以三根為一組數右邊的另一部分。左余一則右余二,左余二則右余一,左余三則右余三。
左 右
1 | 2 |
2 | 1 |
3 | 3 |
再揲的余策或三或六,放在左手中指與食指之間(或將左手指所掛之策放在一邊),然后將左右兩邊的正策合于一處。所余正策會有三種情況,即:
30-3=27 30-6=24
27-3=24 27-6=21
這樣再除以3就可得出9、8、7三個數中的一個。即:
27÷3=9,畫一一一;24 ÷3=8,畫一一;21÷3=7,畫一。
此為一方之位。如此連續共作四次,自上而下排列,則方、州、部、家之位皆成,一首之名可定。
[附記]黃宗羲在《易學象數論·太玄蓍法》中,對王涯、胡雙湖、季彭山三人所論太玄蓍法分別作出評述。黃氏評述王涯說:
左右一揲之余,其掛扐之數,不三即六;三者得三十策,三七之余為九;六者得二十七策,三七之余為六;更無得二十九策可以為八也。然王氏雖謬,不以余策而論,猶為未失其傳也。
黃氏肯定王涯以最后所得正策而求七、八、九的正確性。但同時指出王涯于一揲之后,即合左右正策求七、八、九是錯誤的。因為一揲之后,掛扐之數或三或六,左右正策或三十,或二十七,按王涯三七(二十一)之余,只能得到或九或六,不可能得到八和七,因此說“王氏雖謬,不以余策而論,猶為未失其傳也”。
胡雙湖論太玄揲蓍曰:
三揲有余一、余二、余三,而無余七、余八、余九之理。解者甚多,皆不通。意者子云之法,以余一準七,余二準八,余三準九, 只余一、二、三則七、八、九自定矣。故曰:“余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只倒用一字,故難解。若作余一為七,二為八,三為九,人無不曉矣。
黃宗羲曰:“胡氏舍正策而論余數,失之遠矣。南宋以后,揲蓍者皆尚簡便而置正策,不獨太玄也。”
黃宗羲此論直刺南宋朱熹推崇的掛扐法。大衍筮法中過揲法和掛扐法并存,朱熹推崇掛扐法,是以四五九八掛扐數分陰陽老少以求卦,但其結果與數正策的過揲法相同。此案中胡雙湖解太玄筮有悖于太玄原旨,但黃宗羲否定大衍筮中的掛扐法卻值得商榷。
季彭山論太玄筮,認為,三十六根蓍草,虛三、掛三,實用三十根。將三十根分為左右兩部分,只揲左邊一部分(不揲右邊),所余或一或二或三,“合于所虛之三、所掛之三”,所得或1+3+3=7,或2+3+3=8,或3+3+3=9。如此所得或七或八或九。
黃宗羲評曰:“季氏牽合余數,故展轉愈誤也。” “玄數曰:‘別一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共余,以三搜之,并余于艻。’季氏曰:‘ 掛三,止搜左策’,不亦盡背之乎。”
季彭山別出心裁,掛三和只揲左策,不揲右策,于太玄原文、原注無據,應當加以否定。
綜上所述,在兩千余年的 流傳過程中,太玄筮法曾出現多種注本。季彭山曾指出:“太玄揲法,注家多不能通其說,老泉(北宋蘇洵-引者)以為傳之失者,得其意矣。”雖然眾說紛紜,但筆者認為,張行成、黃宗羲二家之說更為接近太玄原文、原注之意,通過初揲、再揲而“定畫”,是合理的。
北京三式乾坤信息技術研究院名譽院長 楊景磐
2019年5月